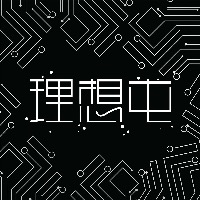大家好,我是@翊瑄Camellia,朋友们都喜欢叫我小球或者球姐。在这里每月发布3-4篇外文译制(思维模型、科技创投、生活哲思和线上写作相关),以及我在海外的数字游民生活、灵修体验和短篇故事等。 我出生于山东济南,2010年去新西兰留学工作,2019年搬到英国和欧洲,过着数字游民的生活,目前为美国一家创投公司远程工作。业余时间喜欢双语创作、看书看球和CrossFit。 我的网站:https://www.camelliayang.com/ 购买成功后,可加入读者群。
在里斯本写下自己|你曾问我家在哪里?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

那天黄昏,28路电车像往常一样叮叮作响,从我身旁穿过。阳光还未完全隐退,特茹河面微光闪动,像心绪起伏的倒影。我站在窄窄的街角,看着电车缓慢驶上坡道,车身刷着黄色油漆,在旧城的砖石之间穿行,一如多年前的它,也一如佩索阿笔下的它。
我没有立即上车,而是让双脚跟着直觉在老城区穿行。熟悉的瓷砖墙、陡峭的阶梯、斑驳的阳台……这里的一切仿佛都藏着一个人留下的气息。我记起佩索阿曾写道:
即便握住了整个世界,我也会将它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。
我明白,他留恋的并不是那条街本身,而是那个每日从那里经过、心中满载思绪的自己。
在下一站,我坐上了电车,靠在木质座椅上,窗外人影交错。电车缓缓行至希亚多站时,我轻轻按铃。那一刻我没有目的,只是想看看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。
巴西人咖啡馆(A Brasileira)在黄昏时分比白日更有温度。门外的铜像旁聚着一小圈游客,而我则径直走了进去。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,木质墙壁与镜面装饰静静地包裹着这个空间,仿佛时间也在这里放慢了脚步。
我点了一杯浓缩咖啡和蛋挞,沉默地坐着,试图捕捉那些曾属于他的瞬间。也许那时他也曾坐在这窗边,也是在疲惫的一天之后,注视街上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,想着如何把混沌的内心写成诗句。
他曾说:
我是遥远边陲并不存在的乡村,是一则从未被写出来的书籍上的书评。
他笔下的人物比他更具轮廓,那些未成形的句子反而透露出最真实的自己。我仿佛看见他就坐在我对面,无需交谈,我们在沉默中达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理解。
咖啡馆的空间不大,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尺度感。木制地板踩下去发出轻响,吊灯将光散在每一个角落,桌上的白瓷杯子发出低沉而克制的亮。窗外是一条慢吞吞的街道,街道上是一个个慢吞吞的灵魂。
佩索阿曾在这里写字。他也许只是像我这样地坐着,听杯子的碰撞声,望着窗外模糊的倒影发呆,然后随便拿起旁边的一张餐巾纸,写下几句别人眼里无关痛痒的句子。他写得太快,好些字也无法辨别,但他还是写了,因为他知道,不写,活不下去。
他写的“道拉多雷斯大街”其实并不远,在希亚多区的下方,若从这边顺着斜坡走十分钟即可抵达。那是一条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街,商店、冰激凌摊、街头艺人轮番更替,却因为他的文字,被赋予了一种私人化的神圣。
我从背包里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,翻到空白页,却迟迟没能落笔。我有些迷茫:到底该写些什么?是眼前这家老咖啡馆的气息,还是此刻对另一个孤独灵魂的想象?
一位服务生经过我身边时,轻声用葡萄牙语说:“Tudo bem?” (你好吗?)
我点点头。是的,我还好。只是忽然意识到,写作这种事,有时候只是为了继续和这个世界有一点联系。不是在传达什么明确的意思,也没有谁非要听见,只是想让那些浮动的感觉有个落点,仅此而已。
我抬头望向窗外,黄昏越发低沉,街灯开始点亮。城市像是换了一层皮,变得温柔而暧昧。
佩索阿的铜像依然坐在门外,那双空洞的眼神望向街道,却好像穿透了我。我忽然有种奇怪的念头:他其实从未离开过这城市。他只是退到了某个时间的背后,等着像我这样的陌生人,在某个黄昏重新与他重逢。
我不再试图妄想写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,只是把本子收起,手指轻轻扫过空了的咖啡杯边缘。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在异乡真正让人感到疲惫的,是太多时候的无法说出口,也没人愿意听。佩索阿则像一面镜子,就这样坐在一旁,无需言语地提醒我:即使没有回应,倾诉依然有意义。
从咖啡馆出来,我沿着加雷特街慢慢走去。行人越来越多,街灯还未亮起,日落把整座城市染成浅橘色。街边的店铺开始收拾,晚餐的香气在空气中飘浮。我没有刻意寻找目的地,任由步伐顺着余晖流动。直到“Bertrand”三个字出现在眼前,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贝特朗书店。
门口那块“世界最古老书店”的标识让我短暂地停顿。许多人在此拍照留念,而我只是站着,静静望着那扇看似普通却厚重的木门,想象两百多年前它第一次开启时的模样。那时候,纸还带着墨香,书页未泛黄,来访者也许穿着长大衣,手拎帽子,怀里夹着信件。
推门而入,外头的喧哗瞬间被隔绝。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旧木头的气息,书架高高矗立,一排排静默伫立着,像是等待被读懂的思想。我没有刻意寻找哪本书,只是在书架之间缓缓走着。手指不时掠过书脊,触碰某种未被命名的命运。
最终,我还是来到了佩索阿作品专区。这是我注定会抵达的地方。那些书安静地排列在一起,封面风格各异,语言各不相同,纸张厚薄不一。但内容,却都散发着他特有的气息,反复、细碎、沉默、不安,像夜晚独自行走时从身后飘来的脚步声。
我抽出一本葡萄牙语版的《Livro do Desassossego》,随手翻开,目光停在某一页时,心跳竟然有些急促:
假如有一天我在经济上变得宽裕,以至于能够自由自在地写作和发表作品,我知道我会想念这种很少写作和根本不能发表的不稳定生活。
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,读了好几遍。
这段话没有在讲述匮乏,却轻轻唤起了那些无人知晓的时光:写不完的草稿、夹在信封背后的只言片语、那些无法说出口的念头。它们也许凌乱、不够完整,却真切得让人无法忽视,像一道深夜里的微光,从沉默中透出,让孤独的人找到片刻共鸣的光亮。
那一瞬间,我想起了自己在飞机上、深夜里,或在快要崩溃的时候,曾把心里最不成形的情绪记在纸上。它们没有任何顺序,也说不上有什么意义,却总能让我觉得,我还活着,哪怕只是以一行歪斜飞舞的文字。
我坐在书店一角的木椅上,心已飘向远方。佩索阿在这座城市建构起他庞大又破碎的宇宙,而我,也正在这里寻找一种可以栖身的形状。那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,而是一种活着的方式:允许自己怀疑,也允许挣扎,同时保留相信的能力,和一点点的温柔。
我想到他一生中虚构出的八十多个异名。他为每一种不同的自己起了名字、写了风格各异的作品,让这些人格在纸上共存,有人写诗,有人写散文,有人冷静如刀,有人混乱如风。他在内心建立了一座小城,让纷杂的情绪各安其位,如同在脑海中默默主持一场持续多年的思想聚会。
书店外天色渐深,昏暗的灯光将街道涂上一层金黄。一位轮廓深沉的男人靠在门边低头看书,发梢晕出一圈柔和的光。他的样子让我又想起佩索阿。他大概也是这样的人吧,站在人群边缘,悄悄看着这个世界的模样,然后老老实实地把那些经历过的片刻写下来,就算是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交代。
我那翻看过的佩索阿的书籍轻轻放回原处,转身离开时,手伸进帆布袋,摸到了我自己的那本小笔记本。我低头一笑,原来它就是我的《不安之书》。它不会出现在书架上,也不会被翻译成任何语言,但它承载着我走过的每一个夜晚、每一场挣扎、那些荒谬的念头和未竟的诗意。
离开书店后,我并没有立刻回家。那天的风不大,却带着一种莫名的游移感,好像空气里混杂着旧日的回忆,也可能只是我的错觉。我记不起是怎么走进那家咖啡馆的,大概只是被它门前的手写招牌吸引:“Welcome, dreamers and strangers.”
小店不大,座位之间也不宽裕,没有书店那种刻意维持的肃静,却有一种让人心安定下来的气息。几位年轻人戴着耳机埋头打字,有人看着电脑屏幕,嘴角轻轻上扬,还有一个金发男孩正把一张明信片贴在墙上。他看见我,像是认出了什么,朝我点了点头,那种眼神就像在对一个老朋友说:你终于来了。
店主特蕾莎站在吧台后面,她的头发盘得有点松,围裙上沾着些咖啡渍,但她的眼神特别明亮。她用英文问我要什么,我说:“一杯Flat White,谢谢。”然后她笑了,说:“我猜你来自南半球。”
那一瞬间我愣住了。是语音暴露了我,还是我身上有着某种异乡者的气息?她递给我咖啡时说:“我在澳大利亚住过一年。”
原来她是捷克人,年轻时在澳洲、荷兰都生活过。两年前,她搬来里斯本,并在这里开设了咖啡馆,说是“想给流动的人们一个能落脚的地方”。她说这座城市像一张老旧却温柔的毛毯,铺在山丘和大海之间,总能给你一种沉稳的安定感。
她笑着说对我说:“我明年可能要去加州卖房子,这家店只是我暂时的家园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,好像这间咖啡馆只是旅途中偶然搭起的一顶帐篷,随时可以收起,再继续上路。
我望着墙角那些风格迥异的物件:一块乌克兰人留下的滑板,一个阿姆斯特丹游客送的十字绣,一幅涂鸦直接画在墙上,据说是一个本地艺术家喝醉后留下的痕迹。这个小小的咖啡馆像是默默收藏了无数段旅途,每样东西都在替它的主人在这个世界发声。
我站在那儿,再次想起佩索阿。他一生没有真正离开过里斯本,却在笔下流浪过整个世界。而我们这些在城市之间迁徙的数字游民,看似漂泊,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扎根,哪怕只是在一个角落放下一本薄薄的自印小书,也像是对这城市说了一句:我曾经在这儿活过。
于是我把笔记本轻轻放在那片“世界的角落”,起身离开时,心里忽然有一种久违的轻盈。那感觉让我想起佩索阿写过的那句:
我并非因为孤独而写作,而是因为写作是我与世界最亲密的接触方式。
夜晚的里斯本像一场无声的转场。灯光亮起,街道收起白日的松散,换上一层午夜的温柔。饭馆门口多了等位的人群,电车的声音也逐渐远去。上城区(Bairro Alto)是夜色里的另一个世界。白天的市井与游客散去之后,它才真正苏醒。酒吧、法朵馆、迷你的剧场在黑暗中悄悄拉开帷幕。
我推开一扇不起眼的小木门,走进一家朋友推荐的法朵馆。屋里光线很暗,木地板踩起来发出轻微响声,一盏吊灯悬在半空,晃着微弱的光。
音乐开始时,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
吉他的前奏像一声叹息,那种从身体深处慢慢升起的叹息,不是怨,也不是苦,只是时间过得太快,心事太过浓重,于是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
女歌手穿着一袭深蓝长裙,站在角落里,没有麦克风,每一个音节却都像是单独为你唱的。她唱的葡语我听不懂,但某种情绪准确地穿透了语言。就像有人站在你身边,用声音轻声告诉你:“我知道你在找什么,虽然你还没说出口。”
我想起苏轼在《前赤壁赋》里写的那句:“其声呜呜然,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;余音袅袅,不绝如缕。”这不就是法朵的质地吗?她们不是用歌声去抵抗命运,而是用它接受命运的轮廓,然后慢慢揉碎,让它变成可以咽下的诗意。
音乐的间歇,我点了一杯红酒。酒很涩,像某些记忆还没发酵好就被饮下。我看着台上歌者的侧脸,忽然想起尼采说过的一句话:
“没有音乐,生命将是一个错误。”
我一直以为自己早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可在这个夜晚,在这间灯光昏暗的法朵馆,它却像一句全新的告白,径直穿过我心里那些难以言说的部分。
歌声继续。我在脑海中暗想,里斯本这座城市的节奏,似乎本就属于夜晚。
葡萄牙人的晚餐总是来得很迟,正宗的法朵也都是从午夜开始。白日总像是在为夜晚真正的生活做准备,而我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:下午写一点东西,傍晚沿着老城区散步,夜里坐在昏暗灯光下听歌。
在这里生活,从不需要讲究效率,它更关心你的感受:你今天累了吗?有没有空陪自己喝一杯?有没有忽然想起一个早已不在身边的人?
从法朵馆出来时,我觉得整个人被夜色重新包裹了一遍。那歌声不会劝你振作,也不试图安慰什么,只是悄悄把你从日常的壳里带了出来。哪怕只是坐在那里,听完一首,也像哭过一场那样,身体松了,心也静了。
我顺着石阶往下走,远处的特茹河泛着微光,耳边还留着刚才的回声,不知道是音乐的尾音,还是心里尚未散去的情绪。我突然想起一个莫名的问题:佩索阿会听法朵吗?
我不确定。但我想,他会懂这种将内心情绪转化为音乐节奏的方式。他用文字安放不安,用八十多个异名容纳寂寞,把无法整合的自我,慢慢雕刻成一座可以代表这座城市的灵魂。
回家的路上,街道空荡,风吹得树影摇晃,橘色的路灯打在湿漉漉的石板上,泛着淡淡的光。没有太多行人,偶尔有一辆车驶过,车灯扫过路面,又迅速隐入夜色。空气里有种刚刚落幕的气息,像一场演出刚结束,观众还未散尽,但舞台已沉入寂静。
我慢慢走上楼,打开门,一股室内残留的暖气扑面而来。我没有立刻开灯,只把窗轻轻推开一条缝,让夜晚的气息渗进来。
我点了一柱熏香,倒了一杯红酒,把自己陷进沙发里。屋里很安静,只有香味在空气里慢慢扩散,像一层温柔的纱,把人包住。
这并不是一个悲伤的夜晚。但在这样的夜色中,记忆却慢慢浮了上来。想起一些没来得及好好告别的人,也想起那些在旅途中遇见、最后各自远行的名字。还有一些人,他们让我在生活里停了下来,迟疑过,绕过路,也原地打过转。
我拿起笔,在纸上写下这样一句话:
“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,并不总是远方。有时,是一首能让我们在原地停留的歌,一个能让我们安静坐下的地方。”
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,才真正走进佩索阿的“异名宇宙”。
一开始只是困惑,一个人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名字写作?那样的写法太破碎了,也太孤独了。我猜想,他也许只是想换一种方式说话,或者给某些无法被表达的东西找一个可以出现的借口。
后来我渐渐明白,他并不是想遮掩自己,而是太清楚,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往往彼此冲突,无法用单一的身份来容纳。他不是创造角色,而是给那些难以安放的部分一个位置,让它们有权利说话、表达、存在。
对佩索阿来说,写作是一种许可,允许自己保持着复杂、矛盾、分裂的特性,如此地以诚相待。
如果我被身份束缚,我就不能够进入想象的世界而创作这个人。
他曾这样写道。
而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,恍若听见了自己多年来未能说出口的自白。
我想起自己这些年写下的东西。不同的身份,不同的语气,不同的语言。有时候是那个在飞机上写诗的旅人,有时候是那个挣扎着重新翻译自己的移民者,还有时候,是那个明明在人群中,却像潜伏者一样观察着他人的冷眼旁观者。
我曾在小说里创造过一个名叫诺拉的女性角色。她没有固定的国籍,也没有被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念束缚。她穿越过四大洲,最终选择在某个小岛隐居。我曾以为她只是我的虚构人物,但后来才明白,她其实是我未曾活出的另一种人生,又或许,她正是我正在活出的人生。
我写她,也是写我自己。那些我无法直视的部分,我让她去经历;那些我不敢说出口的思绪,她代我表达。写作,是我理解生活、保存意识、安置混乱的方式。一旦停笔,我便觉得自己在现实中逐渐消失。
直到我看到有一个人,他比我更彻底、更勇敢地,把“写作即存在”这句话,活成了现实。
我第一次读佩索阿,是在伦敦封城时期的一个下午。他的句子像谜一样自成宇宙。他在死后留下了25000多份手稿,有些是一句诗,有些是一篇文章,有些只是几句含糊的思考。
他的书桌抽屉像装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档案馆。他用八十多个异名完成了一生的对话,那些人格彼此通信、争论、质疑、偶尔互相批评,就像一个人脑海中永不停歇的内心独白被拆解出来,给了它们各自的身体和声音。
我开始慢慢懂得,佩索阿为何总是与人保持距离。有人说他怪,说他不合群、难以亲近。但我读他的文字,感受到的只有一种温柔,那种小心地、不想打扰任何人的自我保护。世界太喧哗,而他心里住着一块极安静的地方。靠得太近,就容易惊扰。他宁愿守着那份静,谁也不让进。
我也害怕吵杂的场合。陌生人靠近时,我常常会下意识地退后一步。我并不是社恐,而是心里堆了太多东西,一时间,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托付。那些情绪太密集了,像塞满抽屉的信,抽出来一张,就有整叠掉落。
那天我去了他的故居。房间不大,却异常清亮,像他的句子一样干净。书桌前的椅子空着,好像他只是刚出去一会儿。书架上满是笔记和藏书,文学、哲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……每一本都是他通向世界的通道。他在小小的空间里,开辟出一个辽阔的意识森林。
我站在桌前,忽然红了眼眶。不知怎的,一股情绪涌上心头,好像找到了某种久违的理解和共鸣。写作者最奢侈的梦想,大概就是能拥有这样一张桌子:一个属于自己、不必解释的角落。
他曾写:
太多的意念飞快地在脑海中闪耀,我只好随身携带着笔记本。即使这样,写满的纸页那么多,还是不免遗失,有时写得太快,好些字也无法辨别。
我理解那种感觉。那些句子不是你决定要写,而是它们自己来找你。你的责任,只是把它们落在纸上。
“我只是一个管道,让文字流经我。”这是我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。那一刻,我不再执着于靠写作定义自己是谁,也不再急于整理出逻辑自洽的自我。我只想给那些来不及命名的念头,留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。
离开佩索阿故居时,天色已经低垂。我沿着他曾经走过的街道慢慢前行,脚步轻缓,像在走进某种幽微的回声里。他在这座城市写下了那么多碎片,而我也终于明白,所谓写作,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创造出什么完整的东西。有时候,它只是一个人在世界面前发出的回应,是对一座城市、一个时代,或一段沉默的回音。
也许我真正寻找的,从来不是一位作家,而是一个像他那样,能让语言生根发芽的地方。而他的文字让我相信,里斯本这座城市一定有某种隐形的维度,专属于那些说不出自己“到底属于哪里”的人。
我曾在伦敦封城的日子里,在线上的读书会讲过他的《不安之书》,那时候我就说,疫情解封后的第一站,我要去里斯本。
那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许诺,给那个在黑暗中还愿意写下一段日记的自己。
现在,我在这里。走过他走过的街道,坐在他曾坐过的咖啡馆,读他留下的残页,听他未曾听完的歌。我不是来朝圣的。我来,是为了和他对话,更是为了和我自己交谈。
清晨五点,我走出公寓。街道空无一人,风吹动树叶,发出细碎的响声。偶尔遇见清洁工人,或者一只悄悄穿过广场的猫。天色渐亮,我坐在石阶上,拿出纸笔,写下一段话:
你曾问我:“你还在寻找家吗?”
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。
不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永远不变的归属,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,自己不再需要那样一个具体的地方。
家,对我来说,不是一个可以据为己有的空间,而是一种在某刻被世界温柔包围的感觉。
我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归属,但我知道如何用写作把自己安放。
我知道如何在混乱的世界里,留一盏灯给自己。我知道如何在纸上建一座城市,在句子里挖一口井,让思绪得以栖息、饮水、流淌。
现在的我,底层悲观,但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因为我还活着,而活着,就拥有一切。
我爱笑,也爱沉默,珍视每一个细小的美好。像是雨天咖啡杯边缓缓升起的热气,像是转角遇见的一对牵手情侣,像是法朵馆里一个眼神的交换。
我曾走过四大洲,没有哪一处真正属于我,但我在创作中建立了自己的根。我的存在,不需要被理解,也不需要被赞美,只要被记录。
这就是真实的我,带刺,却柔软。孤独,却丰盈。
而现在,我终于能说出口,里斯本是一个属于我的城市,不是因为它给了我答案,而是因为它容纳了我的问题。
那么,你的家又在哪里呢?
浅谈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写作、有效沟通和网文小说
写作导师David Perell最近总结了关于「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写作」的思考,简单编译一下:
梗图时代即将到来——大语言模型的幽默感结合图像生成技术,必......
George Mack|30分钟掌握高主观能动性(High Agency)
乔治·麦克(George Mack)是知名市场营销公司Multiply的创始人和首席创意官,他与孵化器公司Y Combinator(简称YC)合作,帮助超过20多家初创公司(包括两家独角兽公司)......
自然相遇,真诚共鸣|交友的艺术与智慧
朋友看我总能在不同城市结识有趣的人,煞有介事地问我:「你的交友策略是什么?」这个问题让我愣住——现代人究竟活得有多累,连交朋友都要制定攻略?这让我想起社交平台上流行的「人脉管理术」......
浅谈AI创意写作、世界旅人和碎片杂谈
Sam Altman在推上说训练了一个在创意写作方面表现很好的新模型,目前还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发布。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被 AI 写的东西震撼到,因为把元小说的感觉拿捏得......
写作≠自由职业?揭开90%创作者不敢说的行业黑箱
最近收到太多相似的私信,字里行间翻涌着相同的焦虑:想靠写作养活自己该怎么做?没人看我还要继续写吗?作为经历过同样困惑的人,今天我想撕开那层美丽的滤镜,与你坦诚地聊聊写作自由职业的真相、陷阱与通关......
品味的魔力:AI时代创作者的核心竞争力
在创作者的世界中,一场静默的革命正在上演。你的书桌前坐着一位不可思议的助手,它既是博学的学者,又是不知疲倦的研究员,随时准备为你提供创作所需的一切养分。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,而是A......
五十年旅行的智慧:凯文·凯利的全球旅行经验分享
简单编译下凯文·凯利在50年旅行途中积累的经验分享:
我已经旅行超过50年,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我曾独自旅行,也曾带领40个朋友组......
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,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,又失去了什么 |数字游民的爱情生活
我一直以为自由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,像空气一样,轻盈地充斥着整个世界。我从不愿停下脚步,也从未真正停留过。每个新城市、新面孔,都能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那样鲜活,那样丰富......
浅谈AI冲击下的知识价值、提升生活质量和女性养生
简单编译下科技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师Ben Thompson这篇关于Deep Research和知识价值的博文:
互联网......